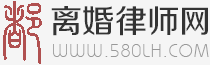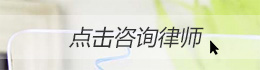
-
夫妻一方约定将个人所有的房屋与另一方共有,但没有办理房产加名登记,赠与方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吗? 2021-12-27 09:51:03 李丽霞
夫妻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全部赠与另一方,因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依照《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而依照《民法典》关于赠与一章的规定,赠与房产的一方可以撤销赠与
-
一方婚前付首付,婚后双方共同还贷的房产,应当如何分割 2021-12-27 09:49:44 罗京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女性思维和价值如何与当下男性化虚构的法律思维和解
来源:离婚律师网 作者:未知 时间:2017-05-15 点击数:4
法学家在试验之后得出了三个结论:1、我们的法律体现了男性的偏见。2、女性思维和价值没有得到体现,且女性思维是完全不同于男性思维的。3、法律所谓的理性、客观、中立是虚幻的,不存在的。
拜读了部分同学的高见,发现不少同学对试验样本的代表性提出了质疑,并由此展开对法学家所得结论的片面性的反驳。不得不承认这是笔者初读案例时没有考虑到的,作为中国应试教育输出的众多产品之一,法学家进行该试验的初衷:女高中生接近成年,对于基本的社会问题有一个初步认知,但尚未接受系统法学教育的“启蒙”,且因其不同的家庭成长环境和经历使这个群体的思维和价值观多样化,勉强能够反映法学家在结论中指出的“女性思维”。而法学家在结论中所提出的法律没有体现的“女性思维”,大概应当是人们固有以来形成的,含有“直觉、主观、情感、柔弱、被动”等特征的女性思维,与所谓“理性、客观、中立、严密、抽象”的法律思维的背离。因此,笔者愚钝,思考之时,并未对试验中样本的选取及设问的妥当性有更多停留,而是对法学家提出的三个命题本身首先产生了疑问,并妄自揣测这是老师“出题的意图”所在。
一、法律究竟是否是理性、抽象、中立的?
溯古至今对法律的认知,各有定论,也各有千秋。但就法律本身而言,不过是人们对人类活动中,合作交往的经验规则的集合总结而已。它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变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诚如约翰·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所述:“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法律规则的产生,可以视作公民‘重叠共识’的结果。”每一个公民都可以看作并应当是法律的参加者和建设者。
既然法律是人际交往的规则,则建立在法律规则之上的法律理论无非是对规则的一种解释。法律适用与诉讼纠纷的解决也只是规则言说和说理对话的过程。正如德国学者考夫曼所言:“只有当规范经由对制定法的建构变成符合事实,而且案件也经由对制定法的建构变成符合规范时,也就是从规范建立一个构成要件以及从案件建立一个‘事实’时,生活事实与规范两者才能进入一种对应中,规范与案件是不同(前者是一个当为,后者是一个存在),它们必须在法律发现中被同等处置。”换言之,法律的建构,总是与法律适用对话交流、难以割裂。而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律推论又不如数学推理一般周全、自足、封闭,这就意味着法律建构的过程中,主观认识和许多不确定因素就糅杂其中,使得法律的理性、客观、中立成为一种只能无限趋近的理想。而实践中,给人们造成法律是理性、中立、客观印象的重要“罪魁祸首”——所谓严密、客观的审判三段论,其功能也仅仅能够表明某个推理过程是正确的,而不是确立过程的结果具备真理性。事实上,司法审判中广泛运用的三段推理,实质上只是论证了裁判者头脑中业已存在的结论。而所谓严密的演绎推理更像是一个面具,让人们相信裁判者是逻辑地推导出的一个新的结论,并因此被说服而接受。正当化过程的运用,其实只是一种“说服的技术”严格的演绎推理的运用并不具有普遍性和连续性。
二、法律中男性偏见——男性化思维如何虚构当前法律?
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证揭开法律“理性、客观、中立”的面纱,而男性化思维如何一步步虚构起当前所谓“理性、客观、中立”的法律,笔者认为“理性论”功不可没。具言之,理性论在认识论上认为法学理论符合科学的理论标准1、法学理论是抽象的。法学理论旨在阐释法律实践中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结构而不是法律实践的某一方面或具体部分。”2、法学理论具有一般性。法学理论总是在追求一套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能够预测未来的规则,使之能够在罔顾所涉地区和社会,过去亦或当下都能够妥当适用。第三,法学理论具有客观性。“就其本质而言,客观性是一个沟通问题,正如你我试图在我们的主观经验中找到的共同点一样。”但又因为科学总被假定为理性、严密、客观的,这与长久以来广泛达成共识的男性思维特征无限吻合,而与被认为是“感性、主观、情感”的女性思维特征背离,科学主义的法学理论观,几乎是以以一种霸权话语甚至是一种价值独断的工具,以“科学”名义,“科学”地将女性拒之门外。在这种近乎垄断地强权论调之下,加上性别角色分配差异的社会文化的长期浸染,女性思维的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怀疑和退却,而这种退却,反而进一步强化了“男性化法律思维正当性”的论断。男性化虚构的法律思维得以固化延续。
三、女性思维到底如何在法律中自持?
在厘清法律的本来面目和法律如何在男性化思维的影响下虚构而来,面对女权主义的勃兴,女性思维到底应当如何在法律中自持?
女性思维总是表现为“直觉、主观、情感、形象”等特征,总体趋向于非理性。这样的观念仿佛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但事实上,被众多科学家用来解释两性认识能力与智力能力上的差异的基础理论,美国神经生理学家R.Sperry的诺贝尔奖的获奖发现“大脑单侧化现象”(亦称“人的脑半球的不对称现象”),也只是表明大脑结构与思维能力相关,但并没有发现男女结构有什么不同。
因此,与其说自然科学为造成这些生物决定性因素提供了依据,笔者更愿意接受,人类行为上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造就的。更极端一点,生物学上的差异论实质上是建立性别偏见的基础上,并以科学的面目而被人们所接受,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来男女思维的对立差异。从方法论上讲,这一过程是解释性的而非证成性的,且有颠倒因果关系之嫌,这一思维过程本身就与其严谨的“男性思维”不符而陷入以主观、感性为特征的所谓的“女性思维”之中。因此,与其说生物学为女性思维与所谓“理性、客观、中立、严密、抽象”的“男性化”的法律思维背离提供了论据,还不如说文化中的性别偏见解释了这种生物性的基础。
通过以上所述,笔者试图说明的是,女性思维是否与男性思维迥异,具有直觉、主观、感性的思维特征,尚且存疑。现在,笔者试图退一步思考,姑且认同女性具有直觉、主观、感性的思维特征,这样的女性思维是否就真的无法在人类法律构建和适用中无法立足。
根据博登海默的研究发现,理性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由于人和事物的关系往往是复杂和模糊不清的,而且人们还会根据不同的观点对它们进行评价,所以在多数情形中,人之理性根本不可能在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疑难情形方面发现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终极正确的答案……如同人类集体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立法和司法这两个过程亦是如此。仅凭理性,立法者和法官并不总是能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可以用来解决某个问题的方法中做出一个确然的和完全令人信服的选择因此,面对理性思维所导致结论的不确定性和临时性,感性思维的弥补作用在最终抉择与正当化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
作更进一步的极端假设,如果认为理性是男性思维的代名词,过分关注抽象的公平正义而缺乏感性思维的男性化法律,最终难免陷入程式化、工具性甚至功利主义的泥潭,其所追求的正义也至多是形式正义。在这种困境之下,感性思维将以其经验的、具体的、更关注个体命运的特点,有效防止规则的僵化所导致的实质不公。女性独特的强调对他人、责任、爱护和义务的关切的关怀道德语言,将是对抽象的男性公正伦理的有益补充。
四、正视差异,让男性思维与女性思维在法律中互补和解
概言之,女性因为生理构造的差异而导致其在法律话语中边缘化的命题并站不住脚,而其因为后期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造就的与男性的差异,恰巧应当如卯榫一般与男性的思维和价值一起在法律中有效契合。差异的解决方案永远不会是差异本身。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发展至今,男性或女性的任一缺席都无法实现,具体到法律的话语语境之下,女权主义法学
要为女性主义寻找法理基础,提供法律的保障,为女性获得应有的平等权利提供共同的司法准则,就必须在正视差异的基础之上,让男性思维与女性思维在法律中互补和解,构建全人类的共同法则,而不是单一的男人的法则或者女人的法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不会一直成为一句束之高阁的政治口号。